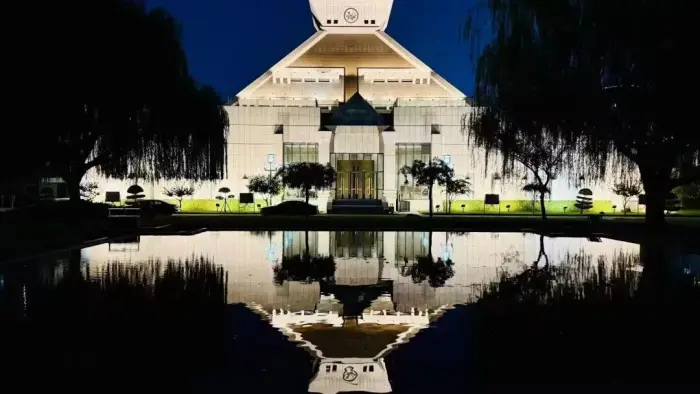现代人洗手,
挤两泵洗手液搓出泡沫,
流水一冲,毛巾一擦,
全程不过两分种。
但若穿越回先秦,
你会发现,
洗手这件小事,
有着极为丰富的礼仪内涵。
周人将洗手称为“沃盥”,
贵族在祭祀、宴飨前必行此礼,
以匜注水、以盘接水,
整套流程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仪式。
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倗之盥匜”,
便凝结着这般对洁净与秩序的极致追求。

倗之盥匜
先秦贵族的洗手礼仪
倗之盥匜,春秋时期青铜用具,
通高约14厘米、腹深约7.6厘米,重1.65公斤,
河南省南阳市淅川下寺楚墓出土,
现藏河南博物院。
这件铜匜体呈圆桃状,曲口宽体,
前有流,流口饰镂空兽首,
后部铸龙形鋬手,平底无足,
腹部装饰蟠虺纹带及锯齿纹,
蟠虺纹间又一道绹索纹,
腹部靠下饰有三角雷纹,
器内底部铸有铭文——
“□(倗)之盥匜”,
宣告着主人的身份。

倗之盥匜
周代贵族在祭祀、宴飨前必行沃盥之礼,
“沃”者,自上而浇之;
“盥”者,手受之而下流于器皿。
浇水的“匜”和接水的“盘”,
共同组成一套盥洗用具。
人们现在仍常用“盥洗”这个词,
“盥”的字形,
就直观地反映出古人洗手的样子。
青铜匜与盘的组合,
既是功能性的“洗手套装”,
又是礼制社会的缩影。
《礼记》载“少者奉盘,长者奉水”,
身份尊卑尽在一倒一接之间。

“奚□单”匜,东周文物,河南博物院藏
考古发现的匜、盘常成对出土,
如河南信阳罗山县窖藏出土的“奚□单”匜与盘,
其有铭文“奚□单自乍宝匜其万年子子孙孙用之”,
道出古人以器物传承礼法的深意。

“奚□单”盘,东周文物,河南博物院藏
洗手不当引发“国际危机”
周代洗手礼的重要性,
在晋文公重耳的典故中可见一斑。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
晋文公重耳即位前曾流亡到秦国,
秦穆公把女儿怀嬴改嫁给他。
某天怀嬴侍奉重耳洗手,
重耳洗完后随手甩去手上残水。
这一举动触怒了怀嬴,
她说:“秦晋匹也,何以卑我?”
意思是说,秦晋两国地位相当,
你凭什么看不起我?
吓得重耳脱衣谢罪来平息争端。

沃盥之礼示意图,图源网络
这场风波的根源,
在于沃盥之礼背后的身份政治。
洗手不仅是清洁,
更是身份确认,
谁来捧匜,
谁来接盘,
皆有严格规范,
稍有不慎便是“非礼”。
重耳本是晋国公子,
流亡多年后行事渐趋随意,
但怀嬴的身份却极为敏感——
她原是重耳侄媳,
这场政治婚姻本就尴尬。
重耳的“甩手”之举,
在怀嬴看来不仅是失礼,
更是对她的轻视和否定。

晋文公复国图(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画家李唐在《晋文公复国图》中,
定格了这一场景:
怀嬴侧身奉匜,
重耳双手微抬,
水流坠入铜盘,
权力与礼仪在无声中完成博弈,
印证了“不知礼,无以立”的周代风尚。
匜的实用化转型
作为一种水器,
青铜匜是适应沃盥之礼的需要而产生的,
最早可追溯到西周中期,
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
战国以后逐渐衰落。
青铜匜的兴衰,
折射出礼仪与实用的消长。

倗之盥匜
西周时期,
匜与盘是贵族专用,
形制庄重,纹饰繁复。
春秋时期,
匜的流槽延长,
足部简化,
甚至出现管状流设计,
实用性显著提升。
至战国中晚期,
无鋬匜出现,
匜用流作柄,
形制更接近后来的瓢具。
秦汉以后,
随着其他制造业的兴起,
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
青铜匜逐渐销声匿迹,
取而代之的是木制、玉制、陶制、瓷质、金银制的匜,
其礼器属性也不复存在,
彻底成为实用器具。

竹雕螭耳匜,故宫博物院藏
从区分阶层的礼器,
到市井百姓的日用品,
匜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见。
与之相应,
洗手这一行为,
也褪去了礼制外衣,
回归卫生本质。
周人以沃盥敬天法祖,
今人以洗手守护健康,
洗手的仪式虽已简化,
但古今对清洁的追求一脉相承。
编辑:许怡童
统筹:梁冰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