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要写袁桥,但你不能只写袁桥。你要写青砖灰瓦间流淌的六百年时光,写明清四合院的雕花窗棂里藏着的家族故事,写寨墙上的每一块老砖如何诉说“修旧如旧”的匠心。要写那440年前的避难碉楼,暗通寨外的地道曾是乱世中的生路,如今成了游客指尖触摸历史的密码。

你要写袁桥,但你不能只写袁桥。你要写新石器时代的陶片沉睡在颍河畔,写550年的古槐树下移民先祖种下的乡愁,写“袁桥”二字从木桥到石桥再到文化符号的嬗变。要写中共登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油灯如何在袁毅故居亮起,红色基因与古寨墙的夯土交融,铸就“登封红一大”的精神地标。

你要写袁桥,但你不能只写袁桥。你要写千亩梨园里春雪般的花海,秋日枝头沉甸甸的香甜如何酿成“梨花节”的狂欢。要写幸福家园社区的高楼如何与古寨门对望,在城镇化浪潮中守住农耕文明的根脉。

你要写袁桥,但你不能只写袁桥。要写慈善工作站每月为老人发退休金的温情,写“焚券高谊”的匾额从明清高悬至今,写袁氏三兄弟4.2亿元的投资如何让古村重生。要写冬至汤圆里揉进的邻里暖意,道德讲堂上“仁义礼智信”的诵读声如何穿透砖墙,织就新时代的文明经纬。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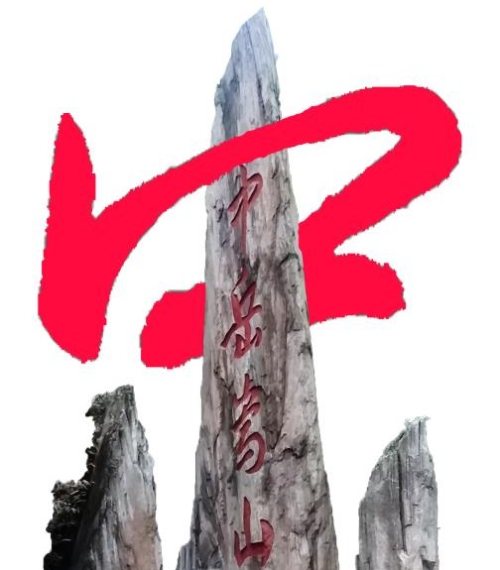 正观登封
正观登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