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俊宏
编|王一粟
一家账上有千亿*现金的车企,在公司楼下搭了个台子就办了自己的十周年庆典。

在活动现场,理想主打一个科技公司的朴实低调,完全不像车企的奢侈豪华。最“撑场面”的节目,是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带着总裁马东辉、CFO李铁、CTO谢炎,四个公司“大Boss”唱了一首《朋友》。相比其他三个人的“腼腆”,领唱的李想借着唱歌释放了不少“压力”。
2025年的理想,正在经历一个全新的阶段。
作为中国汽车新势力中年销量最高,并且首家盈利的车企,理想在2024年底自信满满:一度对2025年的销量充满了乐观。
2025上半年,理想合计交付20.4万辆车,同比增长7.9%。这个成绩,理想显然并不是很满意。今年年初,理想定下的年度排产目标是70万辆。有接近理想人士还曾告诉光锥智能,称今年理想内部曾想“冲一冲”年销百万。面对实际的销量,据媒体报道,理想在今年5月底,选择将年度排产目标下调至64万辆。
但在理想i8发布会之后,市场似乎仍然不满意理想的表现,股价甚至一度大跌10%。
那么,理想真的要跌落神坛了吗?
在浮躁的市场中,人们往往只看到表面的动态来追涨杀跌,却忽略水下更深层的变化。
理想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并不在销量上,而是对技术内功的夯实,更是对未来战略空间的拓展。
“我们最终一定不是标准的汽车企业,我们是一个空间机器人的企业”。
正如李想在7月央视《对话》节目上所说。今年李想在各种场合不停提到AI投入、AI目标、“汽车机器人”等概念,并将AI定义为公司的“一号战略”。
基于这些思考,理想决定在首款纯电SUV汽车——理想i8上首发最新的智驾系统VLA(Vision Language Action Model视觉语言行动模型)。
对于这辆主打6座的家用SUV,理想认为AI是产品最重要的卖点之一。
一年时间,理想的智驾从“端到端”又完成了升级“VLA”的跳跃。
在发布会前,光锥智能受邀参与体验了i8上首发的VLA智驾,并与理想智驾研发团队进行了一次3小时左右的深入交流。
整体体验下来,VLA智驾的行车体验更加舒适。相比端到端智驾,VLA智驾能够实时理解世界并进行逻辑推理,可以提供类似人类专业司机一样的驾驶体验。我们甚至可以,用语音指挥VLA“直接靠边停车”。
“能思考、能沟通、能记忆、能自我提升”。理想汽车自动驾驶研发高级副总裁郎咸朋如此总结当下的这套智驾系统。
成立十年的理想,中场战事不仅仅局限在销量上,更在销量之外的“诗和远方”。
理想i8首发VLA,理想在打什么牌?
理想i8的发布会,智能的含量,远远大于产品。
两个小时的发布会中,理想只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聊了车,剩下三分之二时间讲的全是智能化升级。

为了证明“i”代表的是intelligence(智能),理想掏出了VLA司机大模型和Agent座舱来“护航”。
在“智驾平权”的2025年,辅助驾驶是所有智能汽车不得不拼的一环,但智驾水平是顶尖还是基础,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上周光锥智能体验了搭载VLA司机大模型的理想i8,和目前尚处于测试阶段的“无人穿梭巴士”(所用车型为理想MEGA)。虽然这是该智驾系统落地的第一个版本,但还是能感受到VLA与目前市面上其他高阶智驾的不同。
最大的优点,是智驾跟大语言模型结合,提供了人机共驾的全新交互方式。
VLA把大语言模型的能力,融入到交互和智驾整个流程中。
例如说“靠边停车”,汽车就会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说“前进5米”,他就能向前开不多不少5米。如果用户下达了不合适的指令,例如要强行变道或者闯红灯,汽车还会语音回复说不能这么做,并且还给出用户一个充分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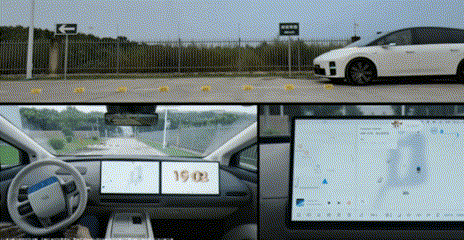
表面上看跟语音转化成语义命令激活城市NOA差不多,但光锥智能观察车机屏幕发现,VLA其实一直在对外部世界进行实时思考分析。
基本原理上,VLA模型的魅力在于对VA模型(视觉-动作模型,可以理解是端到端)的模仿学习,加了一层语言大模型(L代表language)来解释世界,从而提高整个模型的泛化能力。
具体效果,可以用画画来打比方。
VLA模型知道画“上山的老虎”要体现出巡视地盘的傲气,画“下山虎”要体现威猛霸气。但VA模型由于缺少解释,就不能理解其中差异。甚至,在缺乏训练数据的影响下,VA模型还可能会把小老虎画得凶猛。换到智驾上,就是模型可能会发生误判。
光锥智能注意到,理想i8车机上专门有一块部分显示VLA的深度思考。这些思考包含周边场景观察,当前状态的分析,决策思维链三个部分,VLA在不停地给自己下达新的指令。
在地下停车场情境下,VLA能够认出周围环境的“出口”标识,然后“自己”跟着指示走。这种思维和执行能力,已经是跟任何人类一样了。

在体验中,光锥智能也发现了一些遗憾。
例如体验的路况非常简单,全程没有遇到道路复杂情况。现在的VLA只能理解简单指令,不能响应“停到前面那辆车前面”的指令。乘坐VLA无人穿梭巴士时,车辆在拐弯进入窄路时发生接管。这可能是因为采用的MEGA汽车尺寸较长导致。
但总体来看,VLA的乘坐体验还是非常舒适,整个行驶过程相当稳定,几乎感受不到突然的加减速,算是基本媲美人类专业司机的水平。
除了智驾之外,理想i8还带来了跟Agent结合的智能座舱。
汽车也和手机一样,落地了“可以点外卖”等能执行通用复杂任务的Agent。现在用户能在下班路上开着车“点外卖”,也能要求汽车定制生成信息流卡片,比如梳理一下苏超联赛热点。
这代表着理想的AI大模型也拥有了和PC、手机一样,需求理解、代码生成、信息收集、UI自动设计及自动整合的AI能力。这对于长期只能显示车辆状态的车机屏幕而言,显著提升了信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VLA和智能座舱的升级虽然是理想i8首发,但后续也会OTA到其他车型上。
回到销量上,理想i8对理想来说,是补齐了纯电SUV的一环,无论最后售卖怎么样,都属于增量,而不会影响基本盘。但客观来看,理想i8可能确实不会和理想L系列一样成为一个大爆品。
根据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的数据看,2025年6月,纯电车在30万~40万价位的零售占比只有2.1%,整体只能说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市场。
不过,理想i8的发布或许代表着,理想正在经历从硬件产品到主张软件智能化的转向。毕竟,相比在狭窄市场中厮杀,做大蛋糕要更划算一些。
理想变阵,为了做好智能化?
种种迹象表明,2025年的理想正在谋求从内到外的改变。
理想今年的一系列调整有明确两个方向:其一是公司业务管理权力变得更加明确和集中。其二是理想从组织和战略方面,显著加大了AI的资源支持。
两个变化的目标,是为了让整个理想能更重视AI。
2月,理想原空间 AI 负责人陈伟调任系统与计算群组下设的基座模型部门,担任部门负责人,主导基座模型自研。陈伟的汇报对象从理想智能空间副总裁勾晓菲,转为理想汽车 CTO、系统与计算群组负责人谢炎。原空间 AI 下属的语言智能部负责人江会星接替陈伟,成为空间 AI 负责人,向勾晓菲汇报。
马东辉担任智能汽车战略负责人,负责和智能汽车业务相关的战略目标规划和执行落地。随后,理想开始发布基座模型人才招聘。岗位包括,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深度学习训练框架研发工程师等。
总之这场调整,理想整合了汽车和智能的组织架构,同时扩充并提升了整个AI相关部门的级别。这场调整的效果立竿见影,3月底理想就宣称将开源自研的智能汽车操作系统——星环OS。
按照理想的说法,研发星环OS的初衷是跟特斯拉自研操作系统一样,主要是为了应对前几年汽车行业芯片荒,基于自研系统的可控性和对硬件写入的支持,车企可以适当采用一些“非行业标准件”来达成智能化目标。
简单来说,自研操作系统,方便车企定制智能化的需求。
6月,理想战略委员会又成立了 “空间机器人” 和 “穿戴机器人” 两个新的二级部门,这两个部门均隶属于由高级副总裁范皓宇带领的产品部。另一边,原销售与服务群组将和研发与供应群组合并,成立新的智能汽车群组,对理想汽车智能汽车业务的战略到经营闭环负责。马东辉担任智能汽车群组的负责人,向李想汇报。
这次调整,理想强化了汽车智能座舱(空间机器人)和汽车智能化周边(穿戴机器人)两个属性。
随着理想公司内部组织各自形成经营闭环,李想也开始从汽车相关的产品线、产品部、品牌、战略等事务中“解放出来”,并将更多精力投入AI领域。短短几个月中,李想对汽车AI的认知就变了三次,越来越具象化。
在去年12月,李想在AI Talk谈到,“AGI的终极阶段就是成为‘硅基家人’”。在130天之后,李想解释了“硅基家人”的一个体现,认为智驾VLA应该像一个听得懂话的“司机”。6月理想设立的“空间机器人” 和 “穿戴机器人” 部门,印证了李想此前说的,“一个有效的大模型产品应该能跨越所有设备和服务,发展为能自主使用这些资源的智能体”。
“我们今年在人工智能上的投入预计超过60亿,其中45%投在人工智能的基础建设上,包含了基座模型、推理芯片、操作系统、终端算力和云端算力;55%投在人工智能的产品技术研发上,包含了VLA司机大模型、理想同学智能体、智能座舱、智能工业、智能商业等方面。”李想在理想i8发布会上坦言,虽然我们的模型和算力的效率已经优化到了极致,但是人工智能仍然需要花这么多的钱。

梦想很贵,但依然值得。
理想两年实现智驾赶超,半年多做出VLA ,正是基于前期专注卖车+技术不断投入“打怪升级”的结果。
“如果没有通过实车采集的数据闭环,是没有数据能够去训练世界模型的。理想汽车之所以能够落地VLA模型,是因为我们有12亿公里数据。”郎咸朋对光锥智能说。
坐在理想i8的座舱里,光锥智能也能清晰感受到理想的智能化产品能力。车机上每隔几秒输出的VLA深度思考,不仅代表着理想AI大模型对物理世界认识深度,更是智驾在不断与用户之间建立信任。
商业之外,李想追求更远的“理想”
7月有媒体报道称,理想内部将会考虑废弃此前的PBC管理模式,重新回归OKR模式。
两种管理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PBC更关注结果,而OKR更关注过程。PBC更像是一个业绩对赌协议,要求员工对具体的经营业绩负责。而OKR则是提出一个更高的目标,要求员工达成里程碑意义的动态KR(关键结果)。
可以看到,理想正在放下一些对确定性的执念,转而攻克充满变量的挑战。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或许与理想的发展路径有关。
直到今天为止,理想的成功,其实一直是理想ONE成功的延续。
理想率先用较低研发成本的增程式+“冰箱彩电沙发”初步定义了家用智能SUV的“标准模板”,从而占住中高端智能汽车的生态位。在高端的定位下,理想能够在维持超高毛利率(超过20%)的前提下,快速追求销售规模(L系车型)。
在这种战略模式下,PBC管理模式所注重的销售数字和成本把控,无疑给理想的发展狠狠踩了一脚油门。用可量化的动作打确定性的市场,理想迅速成为第一个盈利的造车新势力。
然而,当下智能汽车市场开始出现不少无法量化的不确定性。
从宏观上说,2025是高阶智驾普及元年,理想也在今天建成了全国3000个超充站和16000根超充桩的补能布局。但当前智驾、座舱智能化和电池技术仍处在重大迭代节点上,舱驾一体、智驾芯片和技术架构、固态电池,每一个变化都可能导致汽车产品定义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是把MEGA的从0到1阶段当成了从1到10阶段去经营,错判了商业验证期与高速发展期的区别;二是公司上下被销量欲望绑架,牺牲了理想原本最擅长的用户价值和经营效率。”
正如李想在今年3月内部信中对MEGA失利的反思,今年的理想才开始适当下调出货预期。在所有智能汽车厂商都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智能化技术研发和纯电普及上,理想决定回到“小步快跑”的OKR模式。从一步步的积累中,理想正在逐步接近智能化领先的目标。
理想的底气,或许是来源于智驾研发的经历。从落地VLA的一次次迭代中,理想收获了相当多的基础能力。

为了让VLA模拟更真实的世界,理想为道路上常见的交通参与者都建立了3D模型,并赋予了Agent能力。这样VLA就能在仿真环境与“真实”的小车进行博弈。
顺着这条思路,理想也发现仿真环境训练智驾是一条相当省钱且高效的捷径。
2023年,理想还没做端到端时,实车测试跑了157万公里,算下来每公里花18块钱,一年花了三四千万。2024年,理想仿真测试跑了500万公里、实车跑了100多万公里,也是花了三千万,算下来每公里5块钱不到。今年,理想基本上就纯是仿真测试了。半年时间测了4000万公里,实车只有2万公里。仿真训练的成本,郎咸朋告诉光锥智能,“5毛钱一公里,就是付个电费,付个服务器的费用。”

“上一代技术能力的上限,是下一代技术能力的起点。”
如同郎咸朋对VLA技术的期望。面向汽车智能化的下个发展阶段,理想显然多了一些耐心和期待。
回看中国智能汽车发展,当下其实已经不再是争分夺秒推出新产品抢占生态位的阶段了。
几年时间,中国自主品牌完成了对合资品牌的狙击。肉眼可见,汽车补能基础设施布局越来越完善,大模型加持下的智能化技术,正在为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功能选项。
“希望能在人工智能的硬件终端领域,推出像iPhone一样创新和令人震撼的产品”。
诚如李想的目标,或许现在的智能汽车还没有来到智能手机iPhone 4的临界点。
当能源形式和智能化硬件配置就能“攒”一台智能汽车的红利期开始消退,越来越多的智能汽车玩家开始在芯片、智能底盘、操作系统等偏长期收益的技术领域下功夫。
成立十周年的理想,也在追求更远的“理想”。
*解释:现金状况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受限制现金、定期存款及短期投资以及计入长期投资的长期定期存款及理财产品。

光锥智能
光锥智能官方正观号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