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尖锐的电话铃声如银刃划破夜色。听筒刚贴上耳际,母亲带着鼻音的声音裹着电流传来:“儿啊,别担心,妈就是睡不着,想听听你的声音。”明明我们同处县城,不过三条街、七道巷的距离,这电话线却像条无形的银河,横亘在我们之间。

窗外月光顺着窗棂蜿蜒爬行,在墙面上投下破碎的银斑。恍惚间,樟木箱里陈年樟脑混着旧军装的气息,与车库小屋里电视散出的温热塑料味,顺着电话线悄然交织。这气味的河,载着我溯流而上——记忆突然撞进炽热的午后。
那时阳光像熔化的金箔,将大地炙烤得发烫。母亲系着粗布围裙,歪斜的草帽下,汗珠顺着晒红的脸颊滚落,“啪嗒”砸进翻松的泥土里。她的呼唤穿透热浪:“快过来,妈给你们留了稠得勺都竖得起的米汤!”米香裹着柴火焦气,混着蓝布衫上咸涩的汗味,至今黏在舌尖。我总躲在老槐树斑驳的影子里,望着田垄间那个佝偻的身影,酸涩像未熟透的青杏漫上心头,却不知如何开口。
记忆忽然跳转到1968年秋。红绸系着同心结,父母共筑爱巢。父亲总把褪色的军装叠得板正,压在樟木箱底,那个带五角星的军用搪瓷杯,成了家里最特殊的物件。此后田间地头,母亲弓着背像头不知疲倦的老牛,手掌被木柄磨得血肉模糊,却从不喊疼。深夜,昏黄的煤油灯在穿堂风里摇晃,她用父亲的旧军装布条缠紧伤口,铁锄入土的沙沙声,混着远处拖拉机的轰鸣,谱成春耕的乐章。而父亲收工回家后,总会用那个搪瓷杯给母亲倒上一碗温水,杯沿的五角星在灯光下微微发亮,映着母亲疲惫却安心的笑容。
分家后不久,父亲调到邻近的乡镇去上班了,母亲也便在一家乡办企业当出纳。天未亮,木格窗蒙着薄霜,屋内算盘声混着灶火响起。她膝头压着铁账本,蓝布衫衣角蹭上墨水,专注地核算着账目。傍晚放学,总能看见她踮着脚在厂门口张望,寒风撩起鬓角的白发,怀里紧紧揣着用旧报纸裹的烤红薯:“快接着!凉了就不甜了。”姐姐从她身后探出头:“妈今天特意烤了两个!”清脆的算盘声与如今电话按键音在耳畔重叠,一个敲打着过去的艰辛,一个诉说着当下的牵挂——这段日子,像一枚带着体温的旧硬币,在时光里被反复摩挲。
母亲的爱藏在琐碎规矩里:不许吃饭吧唧嘴,见人要主动打招呼,做人要挺直腰板……她常说:“做人要像田埂界石,立得直,行得正。”那件蓝布衫上被汗水浸出的云纹,恰似她为人处世的准则。职场里,我拼尽全身力气,却总在泥泞中挣扎,付出与回报的天平永远倾斜,甚至累垮了身体。曾经每当我在深夜的加班灯下喘息,母亲在煤油灯下缠伤口的模样就会浮现在眼前,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教诲,如同暗夜灯塔,即便照不亮我脚下的荆棘,也始终指引着我坚守内心的正直。
2012年冬,寒风撕扯着窗棂。卧室里,父亲卧床不起,母亲铺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覆在他身上。她用温水擦拭父亲的手,粗糙的指尖摩挲着他手背上凸起的血管,像抚平岁月的褶皱:“别怕,有我在。”父亲颤抖着指向樟木箱,搪瓷杯沿的五角星在昏暗里明明灭灭,像极了他渐渐微弱的生命之火。姐姐周末赶来,母女俩低声说话,偶尔传来压抑的啜泣。我隔着电话线,听着母亲强撑的平静,第一次意识到,那个曾在田间不知疲倦的身影,也会在岁月里慢慢弯曲。
如今母亲独居在姐姐用车库改造的房子里,客厅、卧室、厨房、洗澡间都齐全。午、晚时分,老年机总会准时响起:“儿啊,吃饭了没?吃的啥?自个儿照顾好身体……”有时沉默中,电视模糊的台词混着咳嗽声传来,电话线那头的呼吸,像无形纽带系着我们的心。挂断电话,我望着窗外的街道,想象着电话线化作金色溪流,从城市这头蜿蜒流向那头——溪流两岸,是母亲用一生种下的春天。
月光依旧。恍惚间,又听见母亲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原来爱早已织进电话线的纹路里:是烤红薯的温度,是蓝布衫的云纹,是岁月铁账本上永远为我亮起的光。那些浸透汗水的旧时光,藏在蓝布衫褶皱里的温柔,化作生命里最绵长的春汛,在电话线两端生生不息,也在时光长河里永恒流淌,温暖着我的一生。
作者简介:冰溪洋(系笔名),原名杨锡冰,河南信阳商城人,娱评人、资深博主,曾荣获责任中国——人民网2011年度、2012年度十大社会责任博客,人民网2014年度十大微博网友;央视网2011年度最具影响力精英博主奖、2012年度十大人气草根博主奖、2013年度十大草根名博;河南日报社顶端新闻2024年度顶端文学十佳散文创作者、2024顶端人气创作者TOP100;入围“博客十年——影响中国百名博客评选”200名单 。
作者: 冰溪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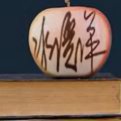
冰溪洋
冰溪洋正观号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