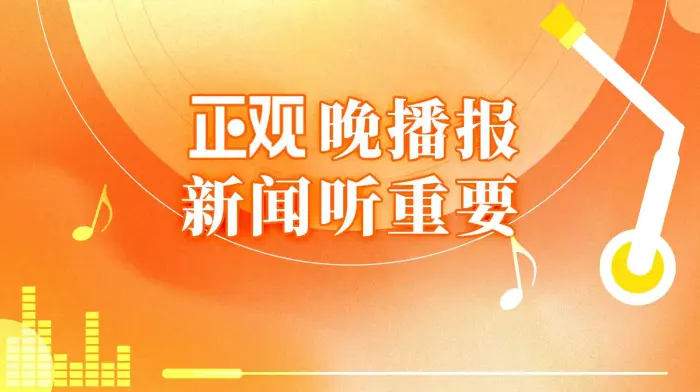凌晨四点,先有一只鸟起头,“喈——”清亮的一声,拖着长尾,划过熹微;跟着另一只试探性地“唧”一声,怯生生的,像是乐师调弦。紧接着,两三声应和从树影里浮出来,不消片刻,这合唱便大胆了起来,高低急徐,竟把一个寂静的小区搅成了天然戏台。
立秋后,晨气凉了些,虫声也掺和进来。最初是蟋蟀,嚯嚯地,像老叟咳嗽,后来便多了许多说不清名目的虫声,咿咿呀呀,与鸟鸣搅在一处,并不觉得杂乱,反倒使作品有了层次。
那段时间失眠,便闭目聆听窗外数米外栾树、山樱树方向传来的自然之声。总想着从各种音色音程里辨别这是只什么鸟,那又是什么鸟,甚至搜索了鸟的叫声,认定有画眉、绣眼、云雀、乌鸫、红耳鹎……我常疑心它们暗中约定了曲谱。每每听得入神,便想向这自然乐团讨个差事——不拘是翻谱子或是敲边鼓,纵使远程办公,也愿意的呀。
真正要识得虫鸟之声的妙处,须得心先静下来。心若不静,便纵有千百只黄莺在耳边啼转,人也只当是聒噪。待得心闲意适,即便是三两声稀疏的雀噪,亦能听出几分天籁的意味来。古人深谙此理,笔下那些动人的鸟鸣,多半是衬在“静”字里的。王维的《鸟鸣涧》便是个中翘楚:“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诗里的声响,是极精微的。人心闲淡,方能察觉桂花坠地的轻触;春山空寂,才容得下月轮初升的步履。而那一声山鸟的惊鸣,恰似一滴墨点入清水,倏忽漾开,反将这无边的静夜晕染得愈发深邃、愈发空灵了。王维之外,亦有他人懂得这寂静中的喧哗。南朝王籍《入若耶溪》中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直白道破了这层玄机。蝉声越是喧聒,愈显得树林幽深;飞鸟偶尔一啼,反而像给山峦套上了消音器。幼时,我的乡邻总嫌夏夜蛙鼓扰眠,而今,久居城市水泥森林之人却视若仙乐,这道理,大抵是相通的。
这般意境,究其根本,是心境的投射。杜甫《绝句》里“两个黄鹂鸣翠柳”,画面热闹鲜艳,但究其底子,仍是诗人暂得安宁时内心生出的那一丝闲趣。若他正慨叹“戎马关山北”,恐怕再多的黄鹂也听不进了。故而非得“人闲”,方能与“桂花落”相遇;若非半夜醒着,到哪里感受如此妙趣之音。音乐人吴金黛深谙此道。她挎着录音设备,深入山林溪涧,经过五年光阴,录得百余种天籁——鸟鸣、蛙鼓、虫嘶、溪流、山羌、飞鼠,无不收纳。她不像寻常采音人,只把自然之声作点缀。却是从白腹秧鸡的啼鸣里找节奏,拿褐鹰枭的叫声定调性,请莫氏树蛙、腹斑蛙担任打击乐手。这般制作出来的《森林狂想曲》,真真是自然与艺术的灵肉交融,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世界。吴金黛说,她收集这些天籁,创作众人能接受的音乐,无非是想引人对这些声音生趣,进而关心自然,保护自然。这是以音乐为桥梁,沟通人心与自然了。
然而,最妙的还不止于此。汪曾祺先生多年前在伊犁听见斑鸠叫,一时动了乡情,想起故乡的斑鸠叫声:“鹁鸪鸪,鹁鸪鸪……”单声叫雨,双声叫晴,这鸟鸣竟与天地节气、人间情思勾连得如此紧密。大约不光因它悦耳,更因它总悄无声息地叩开我们深藏的记忆与情感;原本,它们就是住在我们身体里的音乐啊。
每每想起来,这些不需付费的自然音乐,实在是我们活在世上的一份珍贵而又无价的礼物。
(来源 中国文化报)
统筹:梁冰
编辑:蔡胜文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