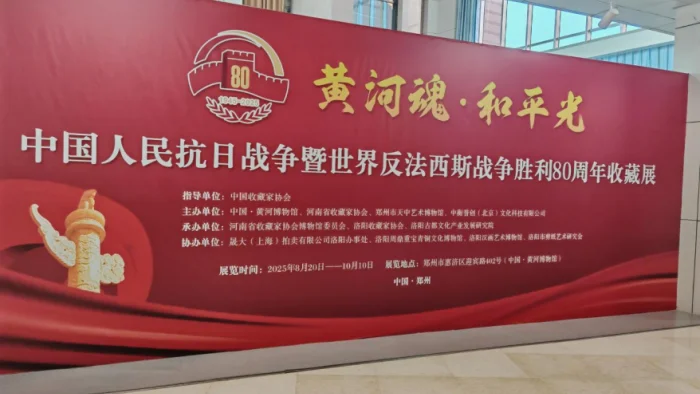在登封市少林办玄天庙村,背靠太室山、面朝少室山的嵩山宝剑传承基地里,66岁的曹延朝师傅总会在清晨走进东院的锻造车间。他戴上厚帆布手套,拿起祖父传下的小锤,对着烧得通红的剑坯“当当”两下,徒弟们便心领神会地抡起大锤,开始一天的劳作。“叮叮当当” 的锻打声穿透晨雾,与2300年前嵩山阳城兵器铸造厂的声响遥遥呼应。
这一幕是曹延朝兑现承诺的日常。从13岁在祖父的铁匠铺拉风箱、和煤的孩童,成长为冲锋陷阵的老兵;从街头摆摊卖太阳帽的创业者,到捧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用半生时光守住了一句嘱托 ——“这门手艺传了上百年,不能到你这一代断了”。如今,家族300多年的铁匠手艺,已从“曹村铁匠铺” 的小作坊,成长为代表嵩山文化的 “活遗产”。嵩山宝剑也从登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中原非遗产业化的典型样本。

家族传承:三代铁匠的手艺基因
曹延朝的锻剑人生始于登封市石道乡术村的一间老铁匠铺。1959年11月27日他出生时,“曹村铁匠铺” 的名号已在周边村落响了近200年 —— 从康熙年间曹氏第一代传人曹廷坯创办 “曹氏剑铺” 起,打铁这门手艺便成了家族的“根”。
祖父曹万青是曹氏第九代传承人,也是曹延朝最早的 “手艺启蒙老师”。那时的铁匠铺是村里的 “热闹地”:农忙时,村民们扛着坏了的锄头、镰刀来维修;农闲时,周边练 “舞狮” 的汉子们会找上门,定制刀枪剑戟等兵器。登封是武术之乡,石道乡周边五六个村都有 “舞狮” 习俗,与南方 “文狮” 不同,当地 “舞狮” 讲究 “兵器伴舞”,耍枪、耍刀、耍九节鞭是标配,每到冬天,铁匠铺的兵器订单便多了起来。
13岁那年,曹延朝第一次走进铁匠铺。“冬天冷,铺子里生着炉,老暖和了。” 他至今记得,祖父坐在炉边,左手握铁钳夹着铁坯,右手拿小锤,四叔曹文顺(第十代传承人)抡着大锤,“小锤领,大锤跟”,火星溅在青砖地上,很快积起一层 “铁花灰”。他凑过去想帮忙,祖父笑着把拉风箱的拉手递给他:“先把火拉旺,这是打铁的第一步。”
最初,他干的都是杂活:拉风箱、和煤、扫地、给淬过火的兵器浇水降温。偶尔祖父心情好,会教他拿小锤在废铁上敲几下 “找找感觉”,告诉他 “脚步要稳,锤要准,劲要匀,不然毛铁就打不成型”。那时的曹延朝还不懂 “传承”,只觉得 “打铁好玩”,直到四叔的意外离世,才让他隐约明白这门手艺的重量 —— 四叔比他大七八岁,是祖父重点培养的继承人,却因失恋患上精神病,31岁便去世了,祖父的病情也从此加重。
真正让他扛起 “传承” 担子,是在1981年的春天。当时,22岁的曹延朝正在部队服役,接到家中电报“祖父病重”,他连夜请假探亲。推开铁匠铺的门时,往日里硬朗的祖父已躺在病床上,手里还攥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小锤。见他回来,祖父挣扎着坐起身,让奶奶把铁匠铺的炉火烧起来,又拿出一块烧红的铁坯:“我教你铁匠最关键一步,淬火。”
“淬火” 是锻打的关键工序,也是徒弟出师前的最后一道,关乎兵器的硬度与韧性 —— 将锻好的剑坯放在炉火中煅烧后,用嵩山泉水淬火,火候、时间全凭经验。祖父拉着他的手,一点点教他判断火的温度、听泉水淬火的滋滋声:“这道工艺以前只传家里的长子,你四叔走了,你哥参加工作了,以后就全靠你了。” 末了,祖父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延朝,咱曹家打铁这门手艺传了八代,不能到你这代断了。”
这句话成了曹延朝的 “人生契约”。那年冬天,祖父去世;次年秋天,他退伍返乡,行李里除了军功章,还装着祖父留下的小铁锤 —— 那把锤柄已被磨得光滑,握在手里,像握着家族的过往和未来。

军旅商海:铁血匠心与资本积累
离开铁匠铺后,曹延朝的人生先拐向了战场。1978年12月,19岁的他报名参军,次年2月便随部队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没想太多,就觉得军人该上战场。” 他记得,战斗打响那天,炮弹在身边炸开,一块弹片擦过他的太阳穴,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战友要抬他下火线,他却把担架推回去,坚定地说:“轻伤,不耽误打仗。”
战场教会他的不仅是勇敢,还有坚韧不拔的精神。退伍后,他被安排到嵩管委工作,先后参与修建登山路、筹建少林寺招待所。在招待所当餐厅经理时,他凭着 “能啃硬骨头” 的劲,把原本亏损的餐厅变成了盈利单位,后来又升任所长。可就在事业顺风顺水时,他却递交了 “停薪留职申请”——“心里总想着祖父的话,想办个剑厂,可手里没资金,咋办?”
1986年,曹延朝揣着仅有的100多元积蓄,在少林寺附近摆起了地摊。春天卖太阳帽,夏天卖啤酒汽水,秋天一到,他又租了个小门面,开起干菜批发部。“啥赚钱卖啥,不怕累。” 有一年冬天,为了赶在年前囤货,他骑着自行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县城进货,回来时雪下得大,车轱辘被冻住,他就推着车走,到店时鞋袜全湿,脚冻得没了知觉。
两年多下来,他攒下了好几万元 —— 在当时,这是一笔 “巨款”。可他没用来盖房,而是把钱存起来,时常去少林寺周边的市场转悠,寻找更大的商机。那时的少林寺已因电影《少林寺》火了起来,游客多,卖刀剑的商铺也逐渐多了起来,但曹延朝一看便摇头:“卖的都是铁片子做的训练剑,一掰就弯,抖劲大了还会断,算不上真剑。” 整个市场里,只有一家卖龙泉剑的是 “真家伙”,价格却要几百元一把,普通游客根本买不起。
“要是咱能打出又好又便宜的刀剑,肯定有市场。” 他心里的 “锻剑梦” 越来越清晰。1988年春,得知河南省嵩山少林寺武术馆招懂经营的人,他立刻报名——“武术馆里都是练武术的高手,能接触到真正懂剑的人,还能积累人脉。”

剑厂创办:武术馆起步到产业化
走进河南省嵩山少林寺武术馆的曹延朝,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有经商经验,馆里让他创办 “劳动服务公司”,开了一家旅游商品门市、一家日用品商店和一个拳击武馆,主营武术器材和纪念品。他把门市的重点放在 “刀剑” 上,一边卖龙泉刀剑,一边暗中观察市场需求:武术馆周边的武术学校慢慢多了起来,大的上千人,小的几百人,学生们需要表演用的刀、枪、剑、戟,可市面上的 “训练剑” 质量太差,常有人来门市问 “有没有好点的刀剑”。
“时机到了。”1993年,登封县(当时未设市)出台政策,鼓励 “事业单位创办企业”,武术馆召开动员会,号召职工参与。曹延朝第一个报了名:“我想办个剑厂,锻造‘嵩山宝剑’。”
没人看好他 —— 办厂需要场地、设备、工人,更需要懂锻剑的手艺。可曹延朝有备而来:祖父教的锻造技艺他没丢,这几年攒的人脉能找到懂行的师傅,摆摊赚的钱能买设备。武术馆领导被他的执着打动,把馆内一台地东南角的 7 间瓦房租给他,他自己又出钱建了6间石棉瓦房,用来锻剑和磨剑。“先试试,干不好再说。”
1993年冬天,“嵩山少林寺武术馆宝剑厂”(嵩山宝剑厂前身)正式筹建。没有现成的生产线,他就照着祖父铁匠铺的样子,砌炉火、买铁钳和铁砧子;找不到熟练的锻打工人,他就从乡下找了几个会打铁的老乡,手把手教他们锻剑工序;为了保证剑的质量,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嵩山脚下挑泉水 —— 祖父说过,“嵩山泉水淬火,剑才够硬”。
1994年春天,第一把嵩山宝剑出炉了。那是一把仿汉剑,剑身经锻、锤、锉、磨等20多道工序,用嵩山泉水淬火后,泛着寒光。他拿着剑去武术学校试卖,校长用剑劈了一下木柴,剑身没弯,木柴却断成两截:“这剑好!多少钱一把?”“100 块。” 曹延朝报了个比龙泉剑低 1/3 的价格,校长当场订了10把。
第一批剑卖完后,订单陆续找上门。第二年他扩大生产,把10多间房屋分成 “锻造车间”“研磨车间”“装配车间”“木工车间”,工人从6人增加到17人,年产量从几百把升到几千把。为了区别于龙泉剑,他先后注册了 “少武”“嵩山” 商标,又陆续注册 “中岳嵩山”“嵩山宝剑”—— 当时 “宝剑” 属于行业名称,按规定不能注册,他托人找中介,花了高价才把 “嵩山宝剑” 四个字注册下来,成了少数能合法使用该名称的企业。
2000年前后,嵩山宝剑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仅武术学校、旅游景区来订货,连政府部门也把它作为地方特色礼品 ——2010年前后,嵩山宝剑先后被赠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新加坡前总统纳丹等中外政要,成了登封的 “文化名片”。2011年,“嵩山少林寺武术馆宝剑厂乾坤分厂” 正式改制为 “登封市嵩山宝剑厂”,“嵩山宝剑” 从 “武术馆下属企业”,变成了独立的品牌企业。

三次搬迁:坚守中的拓荒重生
曹延朝常说:“嵩山宝剑的发展,是‘拆’出来的。” 从1993年建厂到2018年稳定,剑厂历经三次大规模搬迁,每一次都伴随着 “投资打水漂” 的损失,可他从没说过 “放弃”。
第一次搬迁是2005年,因少林寺景区第二次拆迁。当时剑厂已在武术馆的场地运营了12年,他投入十几万元改造车间、添置设备,年产量达8000多把。可拆迁通知下来时,他没有拿到一分钱补偿(因剑厂是集体企业,不在赔偿范围)。“领导找我谈,说景区发展需要,馆里的学生没地住,让你当‘表率’。” 曹延朝没争辩,只是问:“能不能给我找个临时场地?” 焦馆长说:“馆里房子太紧张了,你去登封市区发展吧。”
最终,他找到了少林大道东段路南的康卿两个院,前院用作办公和销售,后院用作生产。但后院原是修车厂,房屋又脏又乱,车间也不够用,曹延朝带着工人翻新平房,又花十几万元盖了十几间临时棚、砌了火炉,再花几万块买新设备,“签了10年合同,想着能长期干下去”。可没想到,8年后,少林路要扩宽,剑厂租的两院又被划入拆迁范围。
第二次搬迁比第一次更难。2013年6月,他拿着仅有的积蓄,又借了几万块,在中岳庙村找了一个小型养殖场、3间门市房和一个独家院,在养殖场内投资近20万元盖了十几间简易车间,还装修了门市房。刚投产没多久,就听说中岳庙可能要拆迁,他开始提前谋划,将2010年在少林办玄天庙村竞拍的一块集体旧厂房提上设计日程(此前因当地规划 “旅游小镇”,一直不让动工)。
第三次搬迁,是他 “赌上全部家当” 的选择。早在2010年,他听说少林办玄天庙村有几间旧厂房和两个院子要拍卖,立刻赶过去。这里背靠太室山,面朝少室山,距登封市区7公里,离少林寺景区只有5公里,交通便利,还能借嵩山的 “灵气”。可旧厂房早已破败:西院6间房子窗户玻璃全碎、电也不通,东院的房子塌了一多半,地面长满杂草,还有村民在里面养牛。“就这儿了。” 曹延朝咬了咬牙,拿出所有积蓄拍下了这块地。
2018年前后,他又贷款投入300万元进行升级改造。西院被改成 “展示 + 销售 + 培训区”,建了展览馆,装了玻璃展柜陈列不同朝代的宝剑仿品;东院保留 “锻造 + 研磨 + 体验区”,复原了祖父时期的铁匠铺,还增加 “研学体验区”,让游客能亲自上手拉风箱、打剑坯。为方便游客参观,他自掏腰包修了门前道路和停车场,光这两项就花了近20万元。
2018年夏天,新基地正式投产。那天,他把祖父留下的小锤挂在锻造车间的墙上,对着锤子鞠了一躬:“爷,咱的铁匠铺,终于安稳了。” 如今,这里不仅是嵩山宝剑的生产传承基地,还是 “登封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每年有上千名学生来体验锻打工艺,曹延朝也常在这里给孩子们讲 “曹氏铁匠铺” 的故事和嵩山宝剑的锻造流程。

非遗传承:从家族手艺到省级瑰宝
2015年9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嵩阳宝剑锻造技艺” 榜上有名,曹延朝也被评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拿到牌匾那天,他特意回了趟术村,在祖父的坟前放了一把新锻造的嵩山宝剑:“爷,咱的手艺,成‘国宝’了。”
这份 “国宝” 荣誉,来得并不容易。从2011年到2015年,他用5年时间完成了 “三级跳”——2011年6月,嵩山宝剑锻造技艺入选登封市级非遗;2013年6月,入选郑州市级非遗;2015年9月,晋级省级非遗。“一般非遗申报需要七八年,咱能这么快,靠的是‘真东西’。” 曹延朝说,申报材料里,既有 “郑韩故城” 遗址出土的战国青铜剑照片,也有祖父传下来的锻打工具,还有他记录的26道古法制作工序 —— 从 “煅坯” 到 “淬火”,每一步都有详细的文字和视频记录。
这26道工序是他从祖父那里学来,又经几十年实践完善的 “宝贝”。“煅、锤、锉、磨、刻、雕、镶、铸…… 少一步都不行。” 他举例说,“折叠锻打” 是嵩山宝剑的核心技艺,需将铁坯加热后反复折叠锻打,最少13次、最多18次,“就像农村蒸馒头揉面,把白面和黑面揉在一起,越揉越匀、越揉越细,剑身上的纹路就是这么来的”;而 “淬火” 必须用嵩山泉水,“泉水的温度和矿物质含量,都影响剑的硬度和韧性,换了别的水,剑就‘没灵气’了”。
为了让技艺 “看得见、摸得着”,曹延朝在玄天庙基地打造了沉浸式传承空间。东院锻造车间里,老风箱、老铁砧、老式火炉一字排开,墙上的 “26道工序流程图” 标注着关键要点;“体验区” 里,游客能在师傅指导下抡锤锻打,孩子们可尝试拉风箱、磨剑、打磨剑鞘等工艺。2020年基地成为 “登封市中小学研学旅行基地” 后,他还设计了 “非遗研学课程”,从刀剑历史发展讲解到实操体验,让孩子们读懂锻剑文化。
他还打破 “家族传承” 局限,广收徒弟。雷朝敏是最早的 “外姓徒弟”,1995年被锻打场景吸引,连续半个月来帮忙,曹延朝看出他的诚意,手把手教他 “小锤领、大锤跟” 的诀窍,还传给他祖父留下的 “锻打口诀”。如今,雷朝敏已能独立完成26道工序,成为第十二代传承人的骨干。加上儿子曹培在内,现厂内6名传承人各有分工:曹培负责电商运营,程朝阳负责打坯,郭正权负责磨剑,崔成生负责装配,大家齐心合力把工艺做得更精。
在曹延朝看来,非遗要 “活”,必须走市场化道路。2013年,他迅速调整产品结构:一方面研发高端收藏剑,采用折叠花纹钢,融入嵩山日出、少林武术等文化元素,提升刀剑的艺术与收藏价值,价格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满足收藏爱好者需求;另一方面开发民用生活类产品,以锻剑的高标准打造菜刀、茶刀、剔骨刀,让 “非遗手艺” 走进寻常百姓家 —— 这些菜刀因硬度高、锋利耐用,很快成了当地农贸市场的网红品,甚至有餐馆一次性订购几十把。
他还主动拥抱互联网浪潮。2013年,他就支持儿子曹培开起淘宝店,把宝剑搬到线上销售,后来又陆续运营天猫、京东旗舰店,组建专业电商团队负责客服、物流和售后。如今,嵩山宝剑的线上销量已占总销量的二分之一,不少网友通过电商平台了解到嵩山宝剑后,还会专程赶到玄天庙基地参观体验。“以前卖剑靠‘等客上门’,现在靠‘主动触达’,互联网让嵩山宝剑的销路宽了十倍不止。” 曹延朝感慨道。

未来规划:守护剑魂的长远布局
如今的曹延朝虽已年过花甲,却仍在为嵩山宝剑的传承奔走。他心里装着两个未完成的心愿,这两个心愿是他对祖父嘱托的延伸,也是对嵩山锻剑文化的长远守护。
第一个心愿是建一座 “嵩山宝剑博物馆”。这些年,他走南闯北收集了不少“宝贝”:有从 “郑韩故城” 遗址周边农户手里淘来的战国青铜剑残片,有明清时期曹氏先辈打造的铁刀、铁斧,还有祖父那代人用过的老铁钳、老铁砧 —— 这些物件上的锈迹、磨损,都是嵩山锻剑史的 “活证据”。他想把这些 “老物件” 集中陈列,再配上登封地区历代锻剑文献、26道锻打工序的动态演示屏,让游客走进博物馆,就能顺着时间线读懂 “嵩山宝剑从哪里来”。为了这个心愿,他已经和登封市文旅部门沟通,还专门请了博物馆设计团队实地考察,“争取3年内把博物馆建起来,让更多人知道嵩山不只有少林功夫,还有千年锻剑的底蕴”。
第二个心愿是编写一套《嵩山宝剑锻造技艺丛书》。过去的传承全靠 “口传心授”,比如 “煅坯时要看火色,红中带黄是火候到了”“折叠锻打时要听声响,‘砰砰’声脆是铁坯匀了”,这些经验性的技巧没有文字记录,全靠徒弟自己 “悟”。曹延朝怕时间久了,这些 “老诀窍” 会失传,于是从 2021 年开始,他每天晚上都在灯下整理资料。他戴着老花镜,把每道工序的步骤、要点、注意事项都写下来,遇到记不清的细节,就去车间里对着铁炉比画,让徒弟用手机拍下来;遇到专业术语不确定,就去查《中国古代冶金史》《登封文物志》,确保每个表述都准确。“书里不仅要有文字,还要有步骤示意图,最后再附个二维码,扫一下就能看锻打视频。” 他说,等丛书编完,会免费发给徒弟、研学基地的老师,还要捐赠给登封市图书馆,“让想学锻剑的人,都能有本‘工具书’”。
除了这两个心愿,曹延朝还在琢磨 “手艺年轻化” 的事。现在的年轻人大多觉得打铁又苦又累,愿意静下心来学的不多,能坚持干5年以上的更少。为此,他每年冬季都会在酒店或厂里举办3~5期嵩山宝剑锻造技艺培训班,免费提供吃住,上午讲宝剑历史、锻打理论,下午带学员到车间实操,还会穿插讲 “宝剑与荆轲刺秦”“李白咏剑诗” 等故事,让大家先 “感兴趣”,再 “想学”。有个叫李松阳的学生,原本对非遗没什么概念,上完课后主动申请周末来基地帮忙,还跟着雷朝敏学起了 “錾刻图案”。曹延朝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年轻人有想法、有活力、记性好,只要他们愿意学,我就把压箱底的手艺都教给他们。”
他还尝试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播锻剑文化。2023年春,在儿子曹巍的建议下,他开通了 “嵩山宝剑旗舰店”“嵩山锻艺” 两个抖音账号,每天拍一段锻打视频 —— 有时是演示 “折叠锻打” 时的火星四溅,有时是讲解 “泉水淬火” 的原理,有时是和徒弟讨论剑的设计。账号开通才半年,就收获了上万粉丝,不少网友留言:“曹师傅,我能来学打铁吗?”“嵩山宝剑太酷了,想买一把收藏!” 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曹延朝都会让曹培帮忙回复,还会邀请感兴趣的网友来基地免费参观体验。“以前觉得互联网离我们很远,现在才知道,它能让嵩山宝剑走得更远。”

一生坚守:锻剑传艺的匠人本色
66岁的曹延朝手上满是老茧,那是40多年打铁留下的印记 —— 从 13 岁在术村铁匠铺拉风箱,到如今在玄天庙基地教徒弟,这双手,拉过风箱、握过钢枪、握过摆摊用的秤杆,最终,还是牢牢握住了祖父传下的那把小锤。
他常说:“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干了一件事 —— 把曹家的打铁手艺守住,再传下去。”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藏着他一生的坚守:祖父病重时,他承诺 “手艺不能断”,哪怕放弃提干机会,也要退伍返乡圆 “锻剑梦”;剑厂三次搬迁,损失几十万,他没喊过一句苦,只为给手艺找个安稳的 “家”;非遗申报成功后,他没停下脚步,反而四处奔走,就为让更多人知道嵩山宝剑。
如今,嵩山宝剑的年产量稳定在4000~5000把,产品销往全国30多个省市,还出口过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在传承基地的展示厅里,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把 “中华奋斗剑”—— 剑身经18次折叠锻打,装具上雕刻着英雄奋斗图、和平鸽、锦绣中华图案,剑身上还刻着入党誓词。这是2021年建党100周年前夕,曹延朝耗时半年专门锻造的献礼作品,100把 “中华奋斗剑” 分别捐给了郑州博物馆、黄河博物馆、焦裕禄展览馆等几十家单位,以及部分战斗英雄。“这把剑的寓意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努力前行’,能让它承载的精神传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曹延朝说。
每天傍晚,当最后一缕夕阳洒在玄天庙基地的铁匠炉上,曹延朝都会坐在院子里,看着徒弟们收拾工具,听着远处传来的嵩山风声。有时,他会拿起那把祖父传下的小锤,轻轻摩挲着光滑的锤柄,仿佛能听到祖父的声音:“延朝,好样的,手艺没断。”
从术村的 “曹村铁匠铺” 到玄天庙的传承基地,从13岁的孩童到66岁的省级非遗传承人,曹延朝的人生就像一把经过千锤百炼的嵩山宝剑 —— 历经磨砺,却始终保持着坚韧的 “剑魂”。这剑魂,是祖父的嘱托,是曹氏家族300年的手艺传承,更是一位中国匠人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守护。
未来的日子里,曹延朝说:“我还会继续待在基地里,教徒弟锻造、整理传承资料、接待研学的孩子。只要我还能拿起锤,就会一直打下去,直到把这门手艺完完整整地交给下一代,我才安心。”
夕阳下,锻造车间的门缓缓关上,可那 “叮叮当当” 的锻打声,仿佛还在玄天庙村的上空回荡,与嵩山的风声、少阳河的水声交织在一起,成为最动人的非遗传承乐章。
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阎洧涛 文/图
编辑:康迪
统筹:赵青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