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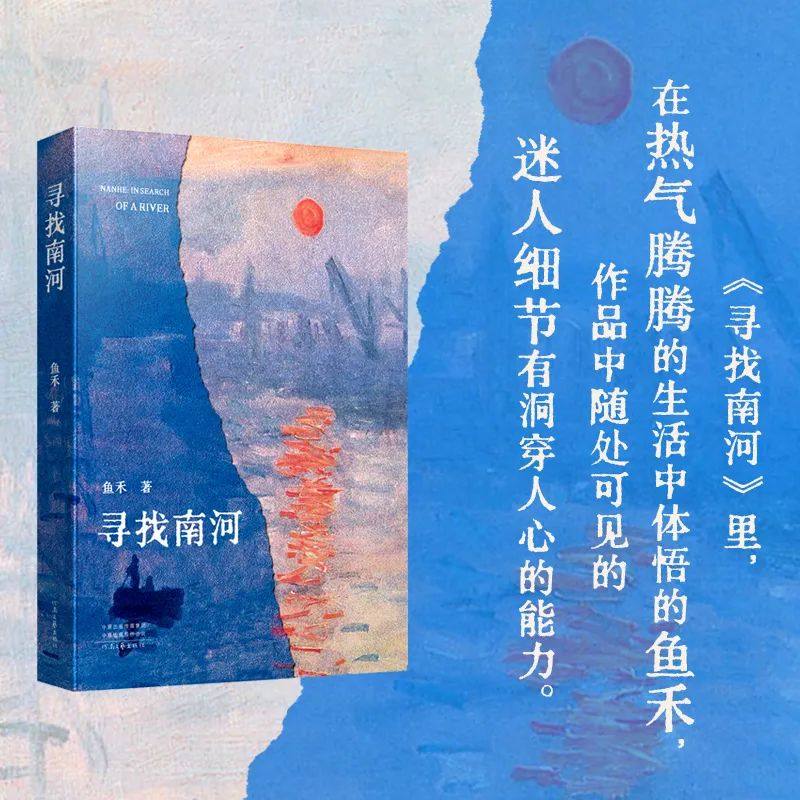
鱼禾自序:有多少南河音书断绝
很多年前,家里养过一只小京巴。
它有着京巴犬特有的大脑袋、大眼睛、大垂耳和小短腿,看上去憨憨的。我并不知道怎么养狗,每天大人上班孩子上学,就把它关在家里,让它在客厅和卫生间活动。下班回家,总能看见被它撕扯得满地都是的碎纸。没心没肺地养了一阵儿,才知道它每天在家里上蹿下跳只是因为太闷了。原来小狗是需要每天牵到室外遛一遛的,养而不遛,等于囚禁。彼时我已经陷入不可开交的忙碌,连孩子都照顾不周,哪里还顾得上小狗呢?只得把它送到乡下老家。隔了小半年再回去,它竟然一眼就认出了我们,冲过来扑到腿上,唧唧哝哝地叫着不肯撒手。我们在老家小住期间,它会日夜跟着,围在脚边团团转。每次都是趁它不注意离开的。我妈说,小京巴也会哭。它发觉不见了我们,会前院后院来来回回地找,确定找不到了,就趴到我们住过的床头,不吃不喝,眼泪从乌黑的大眼睛里流出来,把脸上的毛浸得湿淋淋的。
小京巴在老家养了一年多就死掉了。它一直盼着我们会抱它回来,眼巴巴地等待到死。终是我辜负了它的亲近和盼望,狠心把它丢下了。每想起一只小狗曾经安静地趴在我们住过的床头掉眼泪,都会心疼不已,又伤感又自责。它到底是有感觉的活物啊,既不能有始有终,却把它抱到家里来,不是成心作践吗?
时日滔滔。大半生的时光里曾有过多少这样的辜负,不能想。曾被漫不经心对待的一切,都会化为隐形的雕琢,在后来的自身中找到痕迹。我这粗枝大叶、面硬话冷的人,也总难抵得住终会到来的心一软。在人生行进到某个节点的时候,曾被视若无睹的事物会陡然从遗忘的大幕里破壁而出,断喝一声:呀呀呀——看来!
所有存在的,都会呼叫。所有存在过的,都会在某个时刻,让喊声穿透时间的帘幕,被听见。
若干年前,朋友跟我聊过一件“奇事”——
20世纪60年代末,有个在单位当会计的年轻女人,因为一桩七十多块钱的财务亏空被冤枉,悲愤之下离家出走,从家人和所有熟人视野里“消失”了。由于消息断绝,她也不知道发生在70年代末的形势巨变。直到新世纪初,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一个偏僻山村,这女人被路过的驻队干部偶然遇见,才得澄清往事,辗转回城。要恢复工作已经来不及,原单位便给落实了退休待遇。她与暌违半生的家人终得团聚。但这女人在城里住了大半年,竟然又一次离家出走,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人们到她原来居住的山村寻找也无所获。
据认识她的人说,她回到城里的大半年时间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每天抱着一块纸牌子,到市政府门前去“申冤”。她“申冤”的方式很特别,不哭不闹,也不说话,就站在门岗旁侧的大树下,一站就是一天。她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开始也是有领导问过的,但问来问去,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而且已经恢复了待遇,也就没人再理会了。更何况,一个穿戴齐整的老太太,抱一块两个巴掌大的硬纸壳站在树下,也不影响什么,去管她干吗呢?执意要站,那就让站,中午打份饭别让饿着,天冷了给件军大衣别让冻着,就行了。
乍一听很难理解。如果说几十年前的消失是因为悲愤,后来这一次的决绝是因为什么呢?没有任何具体的事件可以解释。那个尘埋了三十多年的“原因”,与当时发生的许多激烈事件相比,似乎也不严重。但就是这么一件貌似不足挂齿的小事,让一个女人的盛年被整个儿埋没,把她的人生斩成三截。被时间胡搅蛮缠的过往已不可追。所谓冤屈,早已被厚厚的时光淡化。在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后,她要申告的沉冤早已成为过往时代里的小事一桩,几乎化为了纯感受的,在视听的意义上难以成形,不唯无处可诉,而且无可名状。她就是在树下站上一百年,一千年,那件事也还是小事一桩,无可名状,再不会引人注目。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件貌似与己无关的事耿耿于怀,到底还是虚构了一篇《沉冤》来述记此事,心情才算稍稍平复。那晦暗不明的过往啊,它生成了我们今天的形状,是今我的根基。但过往是会坍塌、变形、消失的。在历历雕琢中,自疑也许是最狠辣的刀斧。许多年后才姗姗来迟的反顾,从来都不是自我的进化,而只是属人的自救。
所以有一天,一处被母亲反复提起的20世纪50年代末的工地陡然间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所在,一点也不奇怪。
到后来,母亲提起南河的语气和情形,让我觉得南河在她那里,跟流泪的小京巴、申冤的女人在我心里的情形类似。难以澄清也难以消化的往事,像扎在生活深处的一根刺,并不显眼,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久而久之,它似乎已经被肉身消化,化为许多习焉不察的事物之一,甚至成为隐身物,成为“不存在”。只是偶尔,由于某些不易察觉的机缘,因为意外受到牵扯或碰触,那根刺会在深处隐隐发作,让它与肉身的不和陡然彰显。在我们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一生里,这样的存在何止一端?有多少难以消化之事,到后来不得不“算了”?在不断被“算了”的“小事”中,有多少盼望石沉海底,有多少沉冤再也不得昭雪?
南河在母亲那里也是模糊的、难以概括的。在那一代人生命中,南河意味着什么,一言难尽。那就是长在骨肉中的刺,由于年深日久,既是难以完全化入骨肉的异物,又是不能拔除的原身。直到如今,我已经通过各种资料和多次的实地访问大致弄清了南河的来龙去脉,而母亲,依然说不清当年她花了一个冬天在那里吃苦受罪的南河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过多番查证,我自以为弄清了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958年夏季,黄河大洪水导致豫鲁两省沿河地区和京广交通大动脉险象环生,所以1959年冬天,豫北乡村趁农闲时间,集中了几乎所有青壮年劳力异地调派,从事河道清理和河堤修筑。母亲和老家一带数个村庄的青壮年一起被调派到延津北部黄河故道,修筑黄河左岸的遥堤,为黄河下游可能出现的大洪水预备蓄滞洪区。
可是,我自以为是的这一番求证,在这部书稿审校全部完成以后,被一次偶然阅读再度推翻。在朋友书海上千平方米的藏书馆中间,一本窝在角落、微微积灰、编撰于20世纪末的豫北地方大事记里,居然提到了1959年冬天的这次劳力调派。文中赫然写着:
1959年10月,为支援黄河第五水库大坝工程,浚县成立指挥部,调集卫贤、小河、新镇、钜桥、大赉店公社民工赴延津、汲县施工。次年元月返回。
这里提到的工程形式、劳力调集范围、调派方向、返回时间,与母亲提到的南河工地都是吻合的。原来南河工地的劳作,不是我曾经想象的清理河道,也不是我后来推测的修筑河堤,而是修一座从未投入使用的水库。
这一小节资料,在以前翻阅过的各种记载和回忆里,从来没有见到过,地方志没有,河流志没有,水利志也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也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后来不了了之,并不值得郑重其事地书写。我四处探问这里提到的“黄河第五水库大坝”,所获的答案都是查无此事。有水利部门工作的朋友推测,我写到的这一场劳作,可能是对当地长虹渠段的河底清理和堤坝整修。但我细细对照母亲描述的现场,这个说法很难成立。难怪她一直说不清她那时候干的是什么活,这根本就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苦力啊。
在我们做过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里,有多少是有结果的,又有多少是不了了之的呢?而这许许多多的不了了之,又以怎样的形态凝结在我们的生命之内,在我们的肉身中、在我们的记忆和秉性里留下了难以确认的痕迹?
我坐在郑大工学院那间空阔无人的阅览室里,看着窗外正在风中落叶的梧桐树发愣。书海的藏书如今已堪称汗牛充栋。三十多年前,我们一干人大学毕业都还在嘻哈玩乐的时候,书海和小李已经办起了昨日书店。我已经有好多年不见小李了。当时一起玩的许多人渐渐零落四散。朋友圈水波纹似的不断地扩展开去,只是年过半百还能玩得来也聊得来的,终是屈指可数。我挺羡慕那种能和发小玩到年老的人,但我知道自己做不到。并非刻意要改变,但事实就是在改变,我差不多是个水性杨花的人,对许多人事并不上心。我近旁的人就像水流,总是不断地有新的水流汹涌加入,也有旧的水流悄悄分岔。
生命本身就是浑沌的。在其中发生、成长、衰落、消亡的每一个细节,既微不足道,也分不清青红皂白,它们琐屑而庸常,构成了生命本身的灰度。没有那么多冲突迭起的巧合,没有那么多“原来如此”的清晰与确定。时光只是不断地延伸,我们频频遇到又频频离开,正如大河不断奔赴汪洋,都只是顺从了各自的秉性,极少有过什么格外的原因。
这本小集辑录的文字,大致都涉及一些寻常而未曾分明之事。那些被赋予代称的人,那些林林总总不足挂齿的事与物,我的蟋蟀们,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唯有在字里行间,才会从灰色的“不存在”中显形,成为我们曾经用力活着的印证,亦成为我们将会怀抱惜爱、好好活着的鼓励。为这并不分明之人事物立传,从缤纷落英中照见轮回,从无所谓中觉察紧要,从无数的琐屑庸常中认出证言或预言,或许正是今日散文的道义与天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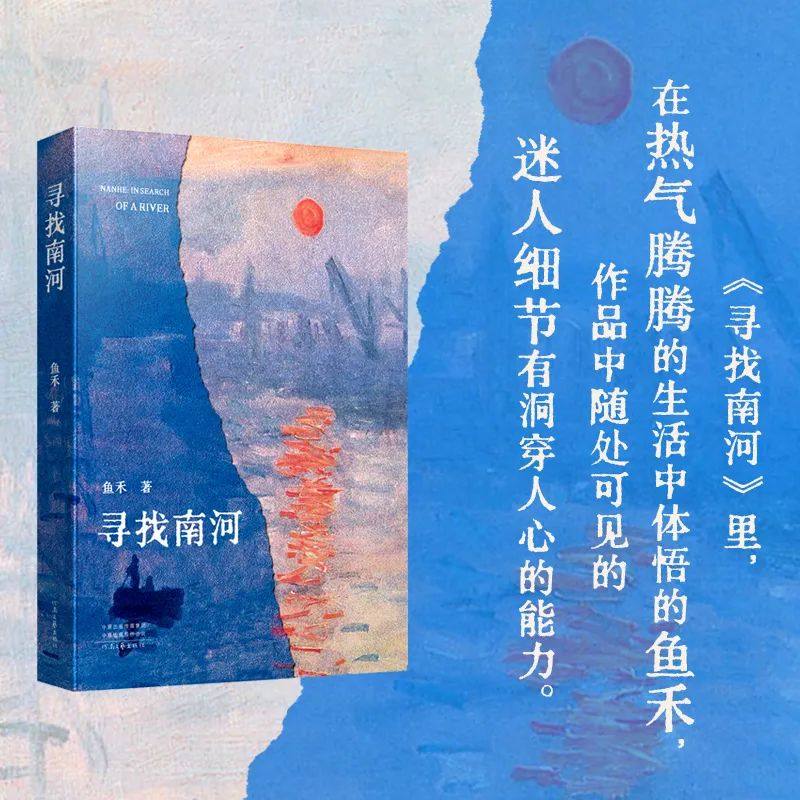
内容简介
《寻找南河》是鱼禾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等期刊的散文作品自选集,共收文九篇。其中收录的作品《界限》获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寻找南河》获2023年度莽原文学奖。随文配有鱼禾创作的彩插九幅。
鱼禾的散文,字字扎实,似行云流水,写意恳切。
九篇散文可以拼成一个鱼禾——一个勇于探索,把探索所得融于心中,慢慢酿它成文的鱼禾;一个对一群孩子,想自我介绍是个“输家”又怕伤到孩子的鱼禾;一个聪慧剔透、照见别人、洞见自己的鱼禾;一个不满于自己身体状态,必须花时间锻炼,不断反躬自省的鱼禾;一个在普通城市女性身上看到神性的创作者……
作品中的字句和意象每每能够洞察人心,发人深省又不动声色。《寻找南河》中的每一篇读起来都轻快灵动,每一篇行文都如同风行水上,举重若轻,深刻剔透。文章是既轻又透的,文字是温柔治愈、引人入胜的。

作者简介
鱼禾,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散文作品《非常在》《私人传说》《大河之上》等七部。散文创作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莽原文学奖等。
编辑推荐
《寻找南河》的九篇文章中,每一篇散文都有自己殊胜的美,这样散点成阵的文字,单独描述其一端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读它的人深入阅读、反复玩赏,才能发现其说不尽的美。
鱼禾的每一篇散文,都有她自己的身影活跃其间,下笔或犹疑,或飒利,总有一些新奇的景象和语词被埋到读者心里,让人想起来禁不住轻轻叹一声。
在《旁骛》《我对不起郝美丽》《大风吹》等文中,她把自己投放到了人群中,心怀悲悯,烛照世情人世的明暗细微之变。

(来源 河南文艺出版社)
统筹:梁冰
编辑:蔡胜文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