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移世易,市声鼎沸。一隅静室,有子据案,眉间清朗,邱才桢笑中藏思。曾执笔于华堂策画繁务,却弃利禄以就幽径。研习之初,不为人知。朋友或劝转他业,或笑其执拗,彼皆坦然应之。曰:“非他图,心安而已。”一念既定,遂投身艺海,潜心六艺,始于笔墨,终归性灵。
书学之路,非一朝之功。取法不专一家,兼收并蓄,不囿碑帖之争,不限朝代之拘。溯自简牍章草,上循二王、怀素,下及鲁直、觉斯;而游走王铎、八大之间,始见自家风貌。初以褚遂良为门径,继而通汉简章草之微理,渐得笔势之真骨。行草为本,文雅为宗,秀逸中含筋骨,沉静里有风神。
沈潜研习,尤喜八大山人。其书法简括不滞,含蓄自持,常于数笔之中,显精神之变。观其行笔,运锋轻重有致,收放纵收之间,气韵生动,流而不滑,涩而不拙。点画之间,已脱章法之旧,独标风骨之新。其人亦如其字,平和中见刚毅,温润里含锋芒。

观墨迹而探流变,览文献而究源流。邱才桢于书画史之学,涉猎既广,析理尤精。每考古帖,必审图像与文辞之交;每读文献,必追时空与人事之合。故其论艺,不拘门径,不执一法,常以多学并进,通贯古今。尝言:“图像与文献,如舟与水,互为依凭,不可偏废。”
讲学之余,远赴西洋。为考敦煌遗卷,旅途万里,踏雪寻碑。英伦藏馆,美域博斋,皆其足迹所至。经卷星散,数目浩繁,披览穷日夜,咀嚼历寒暑。六年心血,终成一论,隋唐写经之书体变迁、章法演变、气息流韵,皆成于笔端。此道久寂,其人点灯独守,遂成此一隅学林之苗。
不惟敦煌,亦探黄山。画史千年,徽风尤炽。取图为证,析景成理,笔底峰壑云烟,眼中时人气骨。初意浪漫,实工尤勤。黄山图像,细察无遗;写生遗稿,比较成论。学界观其稿,咸以为新。盖此项研究,所用方法不拘一格,旁通艺术史与诸社会学说,纵横捭阖,收效斐然。
学而不舍,艺以载道。邱才桢于书法史尤喜论“经典之成”。谓经典非天降之物,乃后人所建之想象,非实录也。曾评《平复帖》《古诗四帖》及“三希堂”所藏名品,以为其流传久远,实因特定语境与意识所塑。更探其成因,如地域情感、政治意图、学术趣味,环环相扣,拨开重重迷雾。

讲席之间,授生有法。非徒传技,实以观念启人。常告学生:研书之道,贵在多维;察艺之路,重在求通。不可偏安一法,不可泥守陈规。古人虽远,然思可通;今人虽近,神或异。以己意会古人之笔,以当代之眼观千载风尘,方为真学。
其为人,素净儒雅。常着素服,微笑含情,步履不疾不徐。入厅堂者,多误其为助教,或询学生证所存。每此,则轻笑不语。笔下之文,神彩飞扬;案上之书,字字珠玑。才识卓然,气质独出。为人所敬,不因外形,而因心性。
书非技艺之末,乃文化之核。墨非笔尖之迹,乃精神之泉。邱才桢自知斯理,故其书风不求艳俗,不逐时风,唯求本真。行笔之际,心无旁骛。观其书,时如清风徐来,时似寒泉喷涌;有时淡若远山,忽又烈似霜锋。正如其人,温润而刚健,谦和而执著。
世道多变,风尘扰扰。其志未改,笔耕不辍。非为虚名,非图高价,只因热爱而不舍。朝夕之间,案头恒有新墨;寒暑交替,砚边常燃旧香。以墨为侣,以书为命。纸上之字,非仅形迹,实为心路之呈;章法之间,透出天地之意。

是以观其学,见其识;察其艺,识其人。邱才桢不惟书家,实为文史之士。其在艺林中深耕细作,于学界中寂然弘道。笔墨之间,写就心灵之履历;学问之中,蕴含文化之传灯。斯人不显于市,然其光芒,久而弥彰。
风雪之夜,案灯独明。笔走龙蛇,心寄千古。昔日临川少子,今朝艺林长松。望其前行之道,或有曲折,终不偏离其志。在时代奔涌中,守一方净土;于浮华世间,保初心不改。是故,墨不干而志不衰,书未成而心犹炽,文不尽而意无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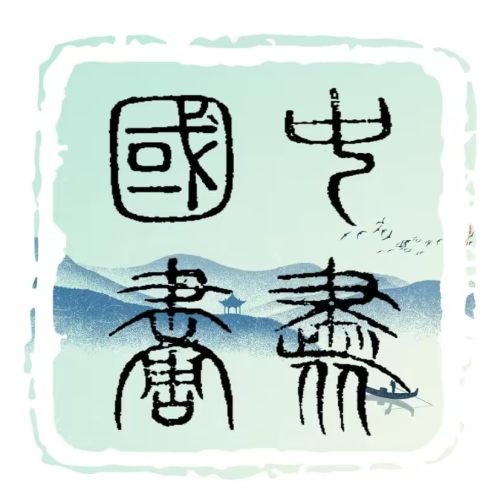
中书国画
中书国画官方正观号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