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_佚名_宫乐图
钤印:
收藏印:鉴藏宝玺: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御书房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
著录书籍:
石渠宝笈续编(御书房),页1977;
故宫书画录(卷五),第三册,页32;
故宫书画图录,第一册,页45-46。
宫中设席,列座成环。帷幄之内,金炉香细,绫罗轻曳,帘影微曛。中设方几,周以绣椅,十余女郎,围坐其旁。或执杯斟茗,或徐言行令;或低眉敛目,或侧首微笑;或扶案凝神,或倚肩偷语。未闻丝竹之响,已觉节奏之中。设宴者非王非侯,居高位者列于左首,戴花冠,衣绣襦,颜色端穆。其余左右,或青衣婢仆,或宫女之属,皆分坐就位,各尽其仪。
案上置金盏玉盘,或酒或果,点缀若星辰。琵琶在手,胡笳低鸣,古筝横列,笙音清远。上首女四人奏而不言,指动处弦声清越,气转间节律如流。立于侧者二,一执拍板,一捧团扇,神色肃然,不与言笑。虽设酒食,而无宴欢之象;虽聚丝竹,而少轻扬之音。设色温润,笔法精谨,描面淡施脂粉,双眉若远山,唇不点朱,鬓不施香,而神采自生,风致横溢。
图中所绘,名曰《宫乐图》,唐人笔也,佚名所作。法出张萱、周昉,承盛唐之风,写后宫之实。女郎之貌,丰腴为尚,眉细如弯,鬓高若云。其妆则元和时式,额留三白,头戴簪花金梳,发髻或堕马之状,或双鬟之制。服则大袖上襦,长裙高系,帛披一肩,轻笼香骨。所饰不艳,所饰不繁,端重而不失妩媚,艳丽而不显妖冶。宫中风尚,于此图可窥一斑。
左方之女,花冠加顶,神态庄严,疑为内庭之首,其余或侍其旁,或居下列。席上之言语若存若无,举止之间,无丝毫怠慢。案下设凳,锦面织金,彩绘云鹤,器用之奢,于细节尽见其贵。屏中背景无山水树石,亦无远景楼阁,专写人物与器具,而层次井然,动静相生,实为工笔之范。
时人温庭筠有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观此图,正足以证之。女郎头饰繁复,光耀交映,非华丽以惑目,而是精致以寓礼。虽未署名,然画风高古,笔迹不凡,设色沉雅,推当出自画院之手,非俗工所能拟。其设构局促而不迫,人物繁而不乱,设景略而不疏,意趣幽深,观者可沉吟久之。
宫中宴集,本属常事,然此图所写,并不在热闹之形,而在冷清之境。女郎貌皆漠然,眉宇间若藏思绪,言不及情,笑不达目,虽手执酒器,实无半分欢娱之意。长席之间,若有声乐回响,实则寂静如水。观者至此,不禁生怜。深宫之内,岁月漫长,晨起听钟鼓,夜息闻笙箫,衣香鬓影之下,实难掩孤寂之情。
唐之宫廷,华丽冠绝,而后宫幽闭之苦,亦不可言。歌舞之中,有别绪千般;宴饮之间,有怨心百种。画者非直写其形,实欲传其神。以宴写寂,以乐写怨,以静写动,以华写哀。此图之妙,正在于斯。世人或叹其设色之丽,勾描之工,未识其中寓意,乃只见其表,不得其深。读《宫乐图》,当如读一阙旧词,初读婉转,久读断肠。
唐人善画仕女,多尚丰美,非独为审美所趋,亦因取象贵妃风仪,贵妃之贵,尚艳尚态,于是女子之像,多丰腴而温润,表柔美之容,寓富贵之气。此图亦承其流风,不拘纤细,不求艳俗,而追形貌之丰盈与体态之丰厚。若仅就妆容、衣饰与仪态而论,此幅已足以复原唐宫风貌,得其神骨,不减堂堂之气。
然其最动人处,不在描绘之精,而在情感之深。女子十人围坐而寡言,饮茶而神凝,听曲而目冷,一室芳华,无一人欢颜。画者用笔极静,而情意流动于眉睫之间。此等寂寥非可语于口,惟丹青可诉于心。千年之后,绢素虽旧,神情未散。阅者如入其间,仿佛可听丝竹之哀,感酒盏之凉,见欢颜背后的幽伤。
《宫乐图》虽小幅,非壁中巨制,然一卷之间,人物十全,情景俱足,动静结合,笔墨凝练,设色清润,为仕女画之典范。其为小屏风之遗件,后裁为轴,尤显其精巧含蓄。画虽佚名,神采可追,风格合于张萱、周昉之制,笔意同于宫中画工之法。其能历经世变而不泯,流入后世而倍珍,正由其超凡脱俗之质,深沉幽咽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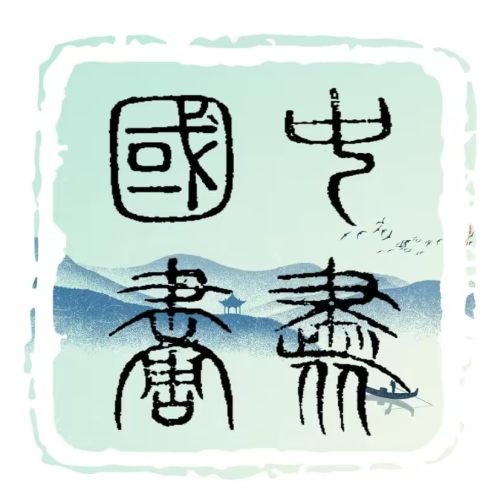
中书国画
中书国画官方正观号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