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虱子为伴的岁月
永城市实验中学于琦

近日,孩子问啥是虱子,我一时语塞,苦找不到标本。便给孩子讲述了几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话说在永城市北15公里陈集,每当逢会,便会听到一位长得酷似曼德拉的老人伛偻着身子、步履蹒跚苍凉地叫卖:“虼子药~虱子药~猪身羊身都管药~不药猪~不药羊~单药虱子这一行......”回想起我身上消失了数年的虱子来,似不觉痒中有痛。
上高中的,生活比较困难。没有多余的衣裳替换,更没有条件去经常洗澡,冷天一到,虱子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了。晚上孤灯下捉虱子便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渐渐衍生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理需要。
虱子带来无尽烦恼,但捕捉的日子也夹杂无限乐趣。说不定白天某个时候,我就会被虱子咬得魂不附体。这时,我会情急之下靠在墙角或大树上蹭,崭新的棉袄很快就露出了“油”。回家后母亲又骂,说干脆光腚算了。虱子捉多了,内衣白衬衫上便留下斑斑血迹。有的人虱子捉不胜捉,冲冠一怒付之一炬,如此,还诞生一条歇后语:烧棉袄杀虱子——得不偿失。艰难的高中生活使我多次品尝过老鼠汤,有时候,买的馍上偶有虱子的光顾。那时对虱子的恨无异于美国佬想绞死萨达姆,欲彻底消灭本拉登。然而,慢慢的,捉虱子竟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心理需求。晚上钻进被窝里埋头捕捉,随着一声声清脆悦耳的“啪啪”声,那红光闪现处,便有了除恶务尽的快意。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中那位指甲上沾满虱子尸体的保姆,也应该是这般快意吧?同时,我又钦佩阿Q与小D咬虱子咬出响来的豪气与果敢。

但是,惩罚这害人虫有多种方式。同桌一次奇痒难耐,脸色大变,急急跑进寝室除下衣服,经过一番穷追能搜,那头酷似花和尚的胖大虱子终于被缉拿归案。如释重负的师兄忿忿地说,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他便用一只碗盖在僻静处,每天一观。时值隆冬,虱子在饥寒交迫中坚守了几天,寿终正寝。我有时候除下虱子用放大镜观察,也渐渐养成了观察小动物的习惯。查字典,得知这小东西不仅咬人,还传播传染病,罪不容诛,干脆火化。用打火机当成火焰喷射器,对着虱子,谈笑间小家伙便灰飞烟灭。我便有了一种生命脆弱和短暂的感慨,有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痛快淋漓。于是,倍加珍惜生命,学会了如何做人。
夜读《晋书》,发现魏晋时代文人士大夫之流竟以有虱为时髦。典型的是,晋明帝时有位少贫贱、博学、好兵书、有大志、生活却不修边幅的名士王猛。当桓温北伐时,王猛披着粗衣去谒见,“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按理说,国家大员理应衣帽整洁举止典雅,可王猛偏偏边挠着痒痒,边摸着虱子谈着话,而桓温并不责怪。“扪虱而谈”这个典故也因而得以流传千古。
敢与王猛的虱子相媲美者当数名士嵇康了。他自称“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洗也。”这位可爱的老先生不洗头不洗脸也不洗澡,终于用自己的身体培育出来了一代又一代的虱子,比现代人用玉米轴芯培育实用菌还高产。杜甫曾疏懒得一月不梳头,连王安石老先生朝见皇帝时虱子都爬到耳朵上,大家也见怪不怪。晚年孤苦凄凉的那位“日晚倦梳头”的宋代女词人呢,是不是也会受闷虱所扰?不修边幅,任由虱子蓬勃发展并与之和谐共处,竟是古代文人墨客的一大雅趣。

魏晋时代文人不洗澡繁育虱子的风尚类似于17世纪法国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是,那时的法国人不洗澡,交往时发现体臭撩人便发明了香水,盛极一时;而此时的中国仅留下了一个“扪虱而谈”的成语,不知是该褒还是贬。
管仲说,“衣食足而知荣辱。”改革开放几十年,国家加快了全面奔向康的步伐。生活水平提高了,卫生意识在增强,虱子渐渐成了久违的稀有动物,平时难觅芳踪了。孩子们问虱子长啥样,我竟一时找不到标本。只能用手机搜虱子的相关信息。从一定意义上说,虱子的消亡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听着衣服褴褛、重度残疾的买药老人苍凉孤苦的吆喝,我又很怜悯他。我想走过去劝他改行,到了跟前,我又犹豫起来:如果他酷爱他的营生,不愿改弦更张,我是否该祝愿他的生意好起来呢?
如今,老人去世数年,他的吆喝声和活跃在民众身上数载的虱子,都风化为了一段往事,走在奔向文明和谐富强的路上,这些过往将会变为痒并痛着的回忆。

河南文苑
河南文苑官方正观号
最新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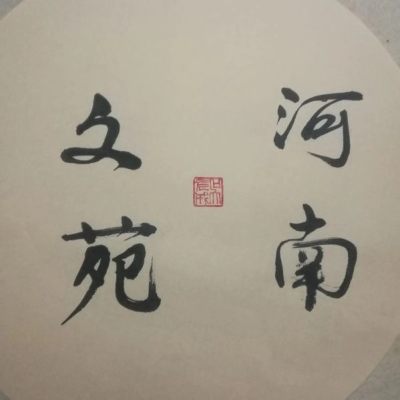
河南文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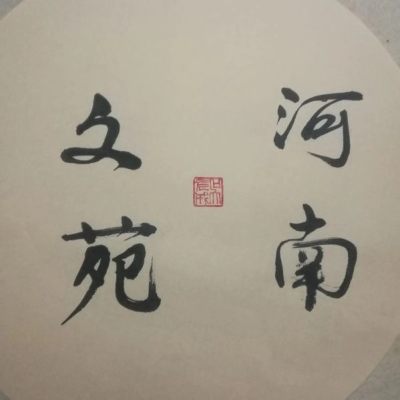
河南文苑
👍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