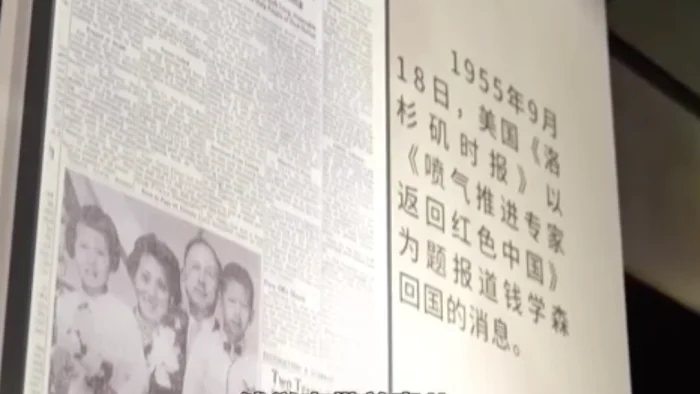问:苗教授,您觉得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的馆藏在甲骨文研究上有哪些独特价值?
苗利娟: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主要收藏的是商代早期的文物,当然也会涉及一些晚期器物。从器物来看,它与商代晚期的器物有很大区别。在文字研究上,这些藏品呈现出早期文字的一些独特特点。
我们现在研究甲骨文,会特别关注字形演变。把字形和文物结合起来,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字的发展起源。我记得袁广阔老师曾在这里做过讲座,他就提出文字并不是从商代晚期才开始出现的,很有可能在夏代时期就已经有了。
他通过器物演变论证了文字中表现的器物形态是早期的,这就为我们博物馆的藏品提供了价值——这些器物为文字发展脉络提供了实物证据。
问:此次选择在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开展甲骨文主题沙龙,您希望观众通过“遗址+甲骨文”的结合,获得怎样不同于书本阅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苗利娟:现在大家都提倡沉浸式体验,我觉得这种方法比自己看书或单纯逛博物馆要好很多。因为有专业人员带着问题引导参观,你会更想深入了解,再加上现场互动,就能对某些问题理解得更透彻。
真正的沉浸式是让你身临其境,去体会古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遗址现场讲述甲骨文,这种结合能创造一种独特的时空对话感。
问:您在研究中发现,哪些甲骨文里的“日常用字”(如数字、方位)与现代人生活关联最紧密,能否用一个有趣的例子为我们讲解一下?
苗利娟:如果要说哪一个最关联,其实很难选择,因为它们都密切相关。数字从一到九,哪个都离不开;方位东西南北中,少了哪个也不行。它们都很有用,都离不开。
这就是甲骨文的神奇之处——三千年前的基础用字,至今仍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问:对于普通观众而言,甲骨文常被看作“高深的学问”,您在沙龙中会通过哪些“接地气”的解读方式,让大家轻松看懂先民“画”出来的汉字基因?
苗利娟:很多人觉得甲骨文高深,但实际上我们学校举办过多期甲骨文进校园活动,年龄最低的受众甚至是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去年九月份,我们组织了一期走进郑大盛和苑幼儿园的活动。
对于五、六岁的孩子,直接要求书写可能不现实,但让他们照着画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要把它当成图画,然后再告诉他们这些图画与现代汉字的关系,这样他们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令我惊讶的是,绝大多数孩子都能认出来。在郑州及附近地区,甲骨文识字基础很好,小朋友们回答非常踊跃,大多数都能认对。现在我甚至觉得需要提高难度了。
问:郑州商代遗址的文字遗存,对理解商朝社会和占卜文化有何关键作用?
苗利娟:目前在郑州商城发现的带文字的甲骨或青铜器数量不是很多,但每件都很关键。它们至少证明在商代早期已经出现了文字。
为什么发现不多?可能与现在的考古发掘进度有关。毕竟郑州商城有90%以上还埋藏在地下,包括王陵等都还没有找到。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发现能够与甲骨文研究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提供更完整的商代社会图景。
问:很多观众可能带着“寻找自己姓氏甲骨文源头”的期待而来,您会如何引导大家通过甲骨文,建立起个人与三千年前商朝文明的情感联结?
苗利娟:很多人都有寻根文化。比如我姓苗,我也很想知道“苗”姓的来历。翻看历史书,我们苗姓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说是楚国贵族有个叫苗贲皇的人,被分封到某个地方,他的子孙就以苗为姓了——以封地作为姓氏。
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可能会觉得“苗”字与禾苗有关。当然这是字的本意,但姓氏来源可能与字义没有直接关系。姓氏来源多种多样,可能与官职、地域有关,还有一些是赐姓,那就更与字义无关了。
通过甲骨文探寻姓氏源头,实际上是在建立一种跨越三千年的情感联结,让我们感受到文明的血脉相承。
作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的副教授,苗利娟博士主要从事商代文字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在她生动的讲述中,甲骨文不再是故纸堆里陌生的符号,而是与每个中国人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从幼儿识图般的认知,到姓氏背后的悠久历史,这位曾出版《汉字中的生肖》、参与编写《安阳博物馆藏甲骨》的学者,正以更加生动的方式,带领人们发现:每个人的日常里,都藏着三千年前的商朝“天机”。
统筹:王绍禹
编辑:蔡胜文

本文(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音乐、视频等)版权归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需转载本文,请后台联系取得授权,并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同时注明来源正观新闻及原作者,并不得将本文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